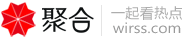尹纪周:“向下”其实是昂扬的虔诚
刘敬行的诗,我向来是有好评的。他的诗不俗,而且很有力度。我和他认识,因为他是记者,很多人眼中颇资深的那种。我算是公众眼里当时很有点儿影响的文化人,他拿诗给我看,语气谦逊“请指导”。没想到看到他的诗,着实让我吃了一吓!他年轻时竟然是住过老山前线猫耳洞的“战地诗人”,字里行间“凛凛然,凝结着钢的意志”。我发自内心的敬佩,鼓励他出诗集,于是有了他的第一本诗集《吉祥鸟在生命的天空飞翔》,后来又出版《淬火时光》。他出诗集,起初的确源自我的肯定,所以两本诗集都收有我给他写的诗评。可能是惺惺相惜,他和我的交情慢慢凝结成肝胆相照。他持续着对我生命的关注,喜我的欢喜,痛我的所痛。我和他逐渐分不清是友情还是亲情。我们有过促膝长谈,他曾感叹我解开了他心里的结。他对我更加的信任,包括这本《向下》诗集出版前后,尽管我远在天涯,还微信多次和我说起以及商定诗集的命名。
“向下”是相当契合我当下思想的。我从传承鲁迅精神的杂文作家转型到“正清和雅”的禅茶文化学者之后,尤其数年任教佛学院,再到全国弘扬禅茶文化,现在我的生活状态几乎呈现一种闲云野鹤状态,愈加倾情于芸芸众生,倾情于譬如他在《向下》诗中所写“泥土里/有蚯蚓 蚂蚁 根和种子/有土豆 花生 萝卜和红薯/有陶片 灰烬与人类的原址”。当刘敬行把散发着墨香的新书《向下》,从故地邢台快递到海南三亚时,我在书中读出了情感、哲思、深沉、厚重、虔诚和悲悯。特别是虔诚,他对生命、父母、爱人、战友、众生、信念、意志、屈原、袁隆平、芦花、老桥、河流等等,都认真到极致,我称之为虔诚。这本书是献给他70岁的最好礼物,尽管我在今年春节期间见到他风采不减,依然地意气风发,但这本《向下》诗集的诗风,在昂扬的基础上多了许多生命的返观内照。他在这本诗集里像一位禅者,试着探究和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。他用大量篇幅,表达着他对生命的尽可能有深度的审视,向读者传递他心中每一个众生的价值,他想和读者一起在以诗言哲语的表述里脉动。
读他的《向下》诗集,其实是在读他对整个世间的虔诚;读出他的虔诚,则会明白他在《火》诗中“明明灭灭都是一种燃烧”的感悟。他的虔诚是“向下”的,他诗的本怀却聚合着能量,散发着向上的力量。我在这本诗集里,找到与他更多的共鸣。我多年徜徉在儒释道传统文化的海洋里,我触摸到禅是活泼泼的大自在、坦荡、洒脱,而非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。他的这本诗集许多的诗篇,尽管不能说是完全的深刻,却不时闪烁着点点亮光,令我击案赞之。
佛教修行讲发菩提心,利益一切众生。我知道刘敬行基本不懂佛学,不过他的心是“向下”的、悲悯的。作为记者他热衷采访小人物,为数百草根人物立传;作为诗人,他的视角亦多在平民和平民眼里的英雄、贤哲。他说他是“火命”,“一生都在火中活着”,而他的这把火有着自己的特质,既有军人的红色基因又传承着民族的历史:“我不溶于水却随和着风/我在风中发热发光/直到被一个风雪夜归人取走/去捂寒冷的冬”(《火》)。他写铁匠,写瓦工、钢筋工,写拾荒人、守墓人,写割草的老人,写劈柴的爷爷,写数猫猫的奶奶,写卖豆腐的老哥,写种茶的夫妻。对于他们,他是那么的知寒知暖,好像他就是他们的血缘亲人,他甚至愿意做他们。这,不就是现实版的“无缘大慈,同体大悲”吗?读他的诗《每一次跪下大地都颤抖一次》,感觉颤抖的不只是大地,还有我和他的内心。“挺直的人生从不屈膝/只是 捡破烂时才双膝跪地/面朝一堆又一堆垃圾”,他写的是一位因骨质增生而行动不便的拾荒老人,“背负沉重的日子/增生的骨质 痛出泪来”。诗人看到他“跪下 便很难再从/尘埃里站起”,好像是感同身受的自己,“每次跪下大地都会颤抖一次”,于是他“每当 看你下跪/我的眼泪就会/跪在地上”。每个字都像在敲打我的心扉,带给我震撼。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,在他的笔下,我同时读出了老人的坚韧不拔。
刘敬行在后记中写道:“让人读懂的诗不一定是好诗,但好诗必须让人读懂,且让读者点赞和心生感慨,或哭或笑或振臂一呼,或低头思考,或细细地品,能品出个中滋味。”作为以“匕首投枪”起家的我,可以用“杂文作家尹纪周”的名义很负责任地说:刘敬行做到了!我想,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和我一样与他同频共振。
因为,他的情怀是家国情怀:“初心 含苞在一朵红岩的梅上/笔管里的血 热得发烫/一滴滴 从我的骨缝里滴答下来”(《笔墨辞——写入党申请书感怀》)。
因为,他关注的是公众的关注:“这一天 所有的稻谷都跪着/把一个戴草帽的背影/叩拜成世上最高的海拔”(《接您回家》)。
因为,他延续的是民族文化的血脉:“以低于香火的姿势/守着‘文曲星’的高度/衣衫 被风撕碎了/用我的肉身肉身风化了/用我膜拜的膝骨/膝骨朽了 也要朽成/圣人坟上的一捧黄土”(《以低于香火的姿势 守着“文曲星”的高度——写在子贡为孔子守墓处》)。
因为,他的孝比我们的孝更刻骨铭心:“每当唤娘的时候/我的声音总是跪着行走”(《唤娘》),他思念父亲到痛处,“便醉成一滩泥/因为只有醉成泥/我才能在泥里见到你”(《把孤独喝醉》)。
何况刘敬行这本诗集,如陈年普洱和白茶,越品越感觉醇厚。他对世间所有的“虔诚”归于素朴,大有返璞归真的豁达。他说:“我内心平静如水,像只天鹅学会把玉扔掉,把泥土抱在怀里”。拥有过,才懂放下。他发现《芦花是河流生出的白发》,“在水里活着/也在水中死去/生与死都是一条河的造化”。他在《一把扇子让一个世界淡定》诗中忆起母亲夏日右手摇的蒲扇,左手把小时候的他揽在臂弯,“扇出了摇篮曲般柔美的风”,从此他跟母亲学会“用一把扇子/让一个世界淡定”。至此,我想说刘敬行从记者、诗人,正在成为一位生命的智者!